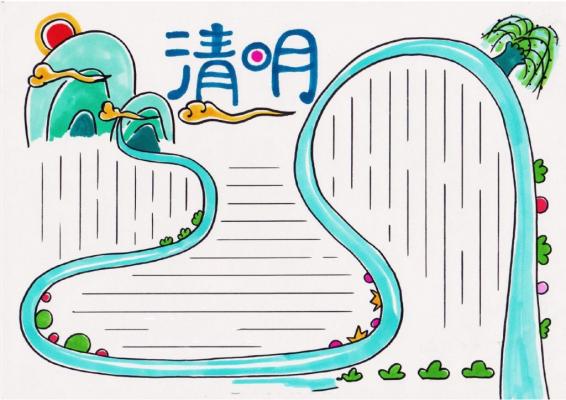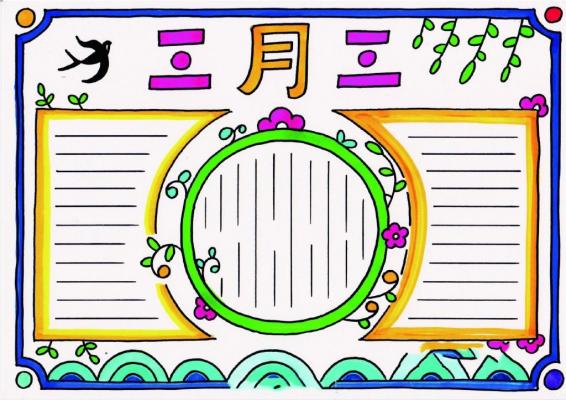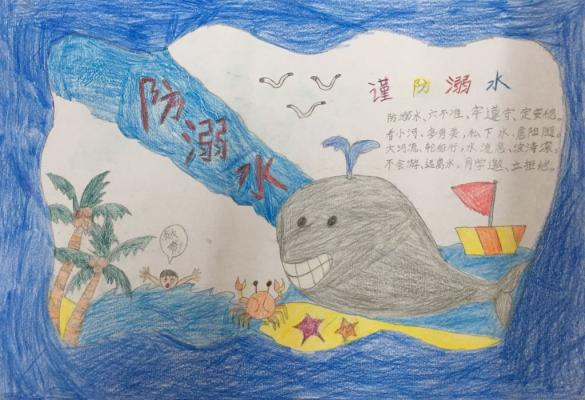国学文化手抄报
国学、经学≠儒学
近年来,谈国学的人渐多,似乎不谈国学不能称为国人。可是,近些年谈国学的人,一谈国学就说儒家之学(简称儒学),以为除了儒学,就没有国学;或是认为,只有儒学才是真正的国学。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徐灏注笺:“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因此古代通常以“儒”称学者,如《字汇·人部》:“儒,学者之称。”以“儒”称谓儒家,只是古代的一种用法,如《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
也就是说,儒家学说是古代服务于帝王统治的教化学说,并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而为老百姓服务的学说。当然,并非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说,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或是主要看作是儒家文化,不仅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将儒家文化中积极的因素给否定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更不是当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无论怎么变化,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或华夏。也就是说,国学应当是中国或华夏历朝历代学术文化之总称。从历史来说,国学不能局限于儒家之学,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学只是与道、墨、法等诸家相并列之一家学说。
百家并存
在学理上,国学何谓却是可以讨论的。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国学教育时增加几分自觉性,使得我们对国学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不会天真的以为穿着长袍马褂逛街就是在讲国学了。曹聚仁先生当年就指出,如果“根本上没有明白国学是个什么,也没想到要去研究国学的原因,只不过因循的盲从,胡乱提倡些国学,做冒牌的圣人之徒”,那“是很危险的”。而前人比如被誉为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的章太炎对国学的看法无疑具有丰富的借鉴意义。
从章太炎本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国学”作为内容当然是贯穿其一辈子的思想主题。从他入俞樾的诂经学社做学生起,直至临终那一刻,他坚持的就是“饭可以不吃,学不可以不讲”。不过,“国学”作为一个概念却不是从来就在他的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早先,作为国粹派主将的章太炎是用“国粹”来指称后来“国学”所代表的内容的。然而,不久他便将概念改换成了“国故”,并作有《国故论衡》。在第三个阶段,才有“国学”的概念的提出。晚年,章太炎还会使用“国性”来称呼国学。显然,就这四个概念的使用而言,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章太炎对“国学”的看法:“国粹”无疑显示了对传统文化的高度崇敬之情。但是,它难以回答“凡是历史上的就一定是好的吗?”这样的疑问。“国故”则似乎略微走向反面,认为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似乎给人某种灰尘仆仆的感觉,比不上“国粹”的古色古香。“国性”所指当然也是历史传统文化。章太炎认为,中国当时面对强敌外逼,只要国性存在,依然有复国的那一天。显然,国性的含义是比较抽象的,不易把握。比较而言,“国学”的提法不仅中立,而且具体。以此为背景,我们似乎也能从“国学”立科而不是“国粹”立科的做法中体会出国家中正的态度。
那么,国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国学的派别”究竟有哪些?他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经学的派别、哲学的派别、文学的派别,这些派别绝非儒学一家能够涵盖的。
章太炎指出,经学包含着“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家,每一家又有各个支系。他本人是古文经学家,认为今文经学所讲的,虽然不完全是宗教,但总体上倾向于此。对此,他是有些不满的。他认为,就“六经”本义而言,“无一非史”。《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是确定无疑的史;《诗经》大部分是为国事而作,只有少量的歌谣,所以也是史;《礼经》记载古代典章制度,是史的一部分;《春秋》胪列事实,中寓褒贬之意,是显明的史;《易经》蕴含着史的精华;《乐经》已经失去,但章太炎揣测它是家在乐谱和制度的,所以也包含着史的特性的。可见,章太炎坚持“六经皆史”说,所以正如汤志钧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国学的派别中章氏并不专列史的派别。由于“六经皆史”,章氏反对对六经“推崇过甚”。这个态度当然和他古文经学的立场密切相关,然而,今日我们再来看“经”,它们究竟是不可移易的“常道”,还是需要与时变化的文本,那是需要仔细考量的,否则一不小心,我们就可能抬举出若干高高在上的教主来,对他们我们只有跪拜的分。
关于哲学,章太炎认为中国古代的儒道法墨名以及佛家可谓哲学的主要派别。他认为,《论语》一半讲伦理道德学,一半是哲理。儒家之中,《孟子》、《荀子》也谈过哲理;老庄的主张,和哲学密切联系;名家大量的涉及“论理学”也即逻辑学;墨子的《经上》《经下》是极好的名学;法家之中韩非的《解老》《喻老》两篇,将他与哲理联系了起来。当然,这是章氏对先秦时期的哲学的刻画。事实上,他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论述言简意赅,揭示了国学哲学之部的丰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