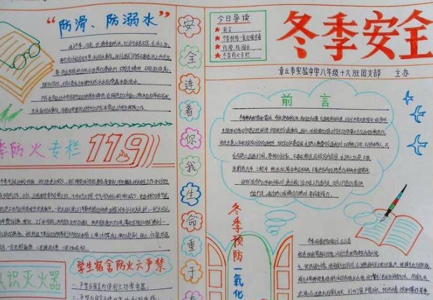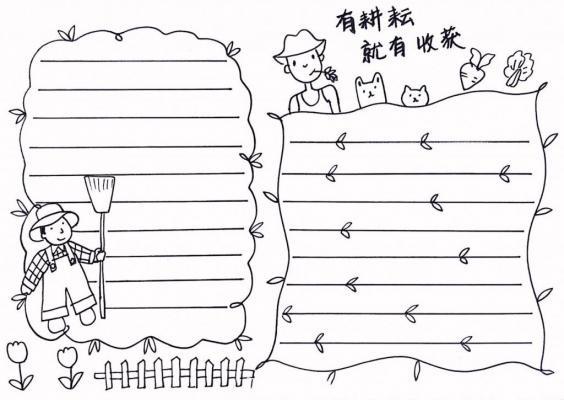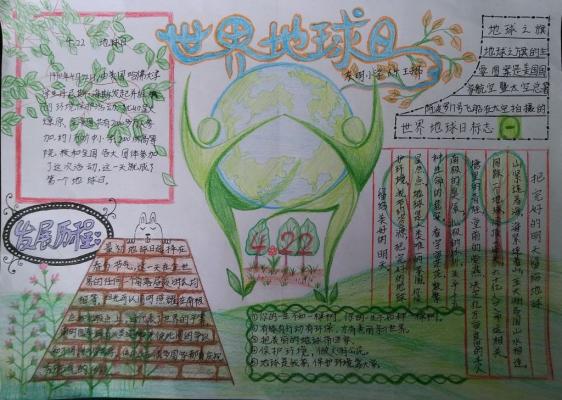自由平等手抄报图片
平等和自由的关系
自由与平等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但起初人们却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法国大革命让“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与信念深入人心之时,并没有人追问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顺序上的孰先孰后、抑或重要程度上的主导与附庸,甚至产生源头上的独立和派生。而实际上,这对孪生子并不那么容易和谐共处。
曾经,自由与平等相伴而行,取得了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最初胜利。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两种价值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被打破,呼啸而来的资本主义在“碾碎了以门第出身为基础的封建性质的不平等之后,又造就了新的巨大的社会差异”。
自由原则允许人们合理合法地占有生产资料,从事生产、贸易活动,由于才能、努力程度和机遇的不同,贫富分化必然产生。过分的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继续蔓延,造成了人们必将面临起点的不平等,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条件,最终失去了自己原本应当享受的自由。正是鉴于这种情况,相当一部分平等主义者认为,仅有“政治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远远不足够的,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要达到实质上的平等,必须实现经济平等,这就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实行再分配。问题在于,如果富有者的财富是合法所得,国家有什么理由将其中一部分占有并用于再分配呢?这无疑侵犯了财富拥有者的自由。我们是否能够以平等的名义牺牲自由?于是,政治哲学家、理论家们之间的分歧和争论由此产生,有人认为不能以放弃自由、侵犯人权为代价来换取平等;有人坚持平等优先,认为只有实现平等,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更有人不仅不接受极端立场,也不满足于中庸之道的权宜之计,力图证明自由与平等的内在一致性。但无论多么精致复杂的理论分析在现实中仍然使兼顾双方缺乏可能性。
这恰恰证明,平等与自由并不一定总是紧密相连。有时候可能存在一种不自由的平等,监狱里的囚徒是平等的,但他们却没有自由。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共和政体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专制政体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是’;而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不是’。” 更多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应该是一种不平等的自由,人们之间是不平等的,但都有一定的自由,区别在于有的人自由多一些,有的人自由少一些。这种不平等的自由或许是一种不完美的自由,但它比完全没有自由或者不自由的平等要好得多——只要这种自由没有太多地脱离平等。
就目前看来,自由或许比平等更易于实现,而平等则比自由更能激起人们的强烈情绪,然而过分地追求平等,尤其是以牺牲自由作为代价去换取平等,最终则可能导致被奴役。正像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担心的那样,人们“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达到狂热的地步……人们会像获得战利品似地去争取平等,像怕被人抢走的宝物似地抱着平等不放。追求平等的激情完全控制了人心,并在人心中扩展和弥漫。这时,你不能警告他们如此盲目地专门追求平等将会失去最宝贵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你也不能向他们指明如此只顾平等会使自由从手中丢掉,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平等,或者说他们看到天地间最值得羡慕的东西只有平等”。“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我国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也正是重视平等而轻视自由的典型体现。
当然,过于崇尚自由而忽视平等也必然带来弊端,一个人过于自由往往会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最终在经济领域导致社会贫富过于悬殊。法国学者德萨米说:“社会法律的设立,决不是为了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恰恰相反,而是为了保护弱者以抵御强者,保障他们获得全部权利。”这无疑有力地证明了平等所体现的社会正义。
任何健全的社会追求的都是自由与平等的结合,然而,“自由和平等之间没有一个天然的平衡点,也没有任何一种能使两者同时达到最大化的方法”。早在19世纪资本主义刚开始蓬勃发展之时,托克维尔就明确指出,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状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根除的”。 当二者出现矛盾时,正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自由一般应该成为更优先考虑的价值,但同时不应超越“平等的基本界限”,因为完全不平等的自由是任何正常人都难以接受的,但完全平等的自由也往往很难实现。